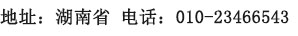儿童哮喘的异质性与靶向治疗研究进展
儿童支气管哮喘(简称哮喘)是一种异质性疾病,包括临床外表型、内表型的生物学靶标和治疗反应不同。儿童诱发哮喘的高危因素复杂且难于识别,年龄跨度大差别明显,多数有吸入技术不当或治疗依从性差,也有因哮喘本身导致难治性问题。尤其是5岁以下儿童哮喘的临床表型具有可变性,不同于青少年和成人期哮喘。因此儿童哮喘的诊断需结合年龄特点,强调首先排除引起喘息的其他疾病。靶向治疗策略是根据儿童哮喘异质性特点,首先去除或避免诱因和病因,基于全球哮喘管理创议(GINA)方案;对于儿童难治性哮喘,可选用生物制剂进行个体化靶向治疗,并观察和评估治疗反应。
支气管哮喘(简称哮喘)是一种具有异质性的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。全球儿童哮喘患病率逐年增高,给患儿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。一项随访50年的出生队列研究发现,儿童期哮喘至成人期缓解率仅为15%,不同的临床结局和肺功能差异与儿童期哮喘的严重度和异质性有关。儿童哮喘的异质性,表现为临床外表型、内表型和治疗反应的差异。诱发哮喘的因素复杂且难于识别,儿童年龄的跨度大且差异明显,多数有吸入技术不当或治疗依从性问题,也有重症难治性哮喘的类型。尤其是5岁以下儿童哮喘,其特点不同于青少年期和成人期哮喘。因此儿童哮喘的诊断需结合年龄特点,并首先要排除其他疾病。靶向治疗是基于哮喘异质性特点和生物学靶标,对哮喘患儿进行个体化靶向性治疗。现结合近年儿童哮喘的诊治研究进展,对哮喘的异质性和靶向治疗策略综述如下。
一、基于临床外表型识别哮喘高危因素
哮喘外表型的异质性,表现在临床症状、病程演变趋势、肺功能指标的变化和环境诱发因素对哮喘发病的影响。5岁以下儿童的呼吸生理和免疫功能还未发育成熟,且不能开展常规肺功能和支气管激发试验,因此年幼儿期的哮喘诊断比较困难。自年全球哮喘管理创议(GINA)单独列出5岁以下儿童哮喘管理指南开始,国内外基于出生队列研究总结出许多临床分型,较公认的两种分型是:(1)按症状表现形式:分为发作性喘息(病毒诱发)和多因性喘息(多因素诱发),但年幼儿期的症状具有可变性,随年龄增长多数有变化;(2)按病程演变趋势:分为早期一过性喘息、早期起病的持续性喘息(3岁前起病)和迟发性喘息/哮喘。但此法仅作为回顾性分析的证据,对于实际临床诊断帮助不大。年GINA建议不用上述两种分型,疑似哮喘患儿可给予诊断性治疗2~3个月,治疗期间哮喘控制良好,但停药后复发则支持哮喘诊断。5岁以上儿童可检测常规肺功能和呼气末一氧化氮(FeNO)水平,可进一步确定哮喘的可逆性气流受限,评估气道高反应性和气道炎症亚型。基于临床表型还可将哮喘分为过敏型哮喘、非过敏型哮喘、迟发型哮喘、不可逆气流受限型哮喘和肥胖型哮喘;非典型哮喘包括咳嗽变异性哮喘、胸闷变异性哮喘和隐匿性哮喘等。
诱发儿童哮喘的高危因素较复杂,儿童哮喘临床研究的热点,包括早期生活环境、生活方式、抗生素使用、呼吸道感染和微生态失调等环境改变对哮喘发病的影响。美国亚特兰大名2~6岁儿童的调查结果显示,早期生活暴露于颗粒物(PM)2.5与增加哮喘风险相关,且较低暴露浓度可产生明显的浓度‐反应曲线。对10个非洲国家名13~14岁儿童的调查发现,母亲吸烟、明火加热、电热供暖、每周3次以上体育运动和每月1次以上使用退热药是哮喘的高危因素;重症哮喘与母亲吸烟、室内养猫、每周3次以上体育运动和每月1次以上使用退热药相关。日本一项对名儿童的回顾性调查发现,胎儿期使用抗生素与3岁前儿童哮喘相关,婴儿期使用抗生素对哮喘的危害可持续到6岁。荷兰一项对名儿童的队列研究发现,6岁前患有下呼吸道感染可增加10岁时患哮喘的风险,3岁前儿童患有下呼吸道感染可影响10岁时的肺功能,提示生命早期呼吸道感染可增加儿童哮喘的风险。南美洲厄瓜多尔的一项对名新生儿的队列研究发现,母孕期蠕虫感染可增加儿童哮喘的风险,但儿童出生后3岁前感染蠕虫则降低5岁时发生哮喘的风险。在美国华盛顿的一项研究发现,不同表型的哮喘患儿鼻腔定植菌种属和丰度均不同,提示人体微生物多样化与哮喘的表型相关。
研究发现母亲为哮喘的婴儿,其肠道菌群以未成熟菌为主,与5岁时发生哮喘有关;若婴儿肠道菌群以成熟菌为主,即使母亲为哮喘,也不会增加哮喘风险;提示肠道微生物可改变具有遗传倾向的哮喘患儿的表型。对名儿童的队列研究发现,7岁时发生哮喘的高危因素有男性、特应性皮炎、宫内烟雾暴露、早产儿和剖宫产术;延迟出生儿和过期产儿是哮喘的保护因素。荷兰的一项研究发现,体质指数(BMI)-Z评分(0.5~1.5)可增加哮喘患儿运动诱发支气管痉挛风险(OR=2.9),尤其是男孩肥胖发生哮喘的风险(OR=4.4),提示肥胖可增加哮喘的风险且有性别差异。
希腊的一项研究发现,肥胖和胰岛素抵抗均与哮喘气道高反应相关,肥胖患儿发生胰岛素抵抗与肺功能损害相关。
二、基于内表型寻找哮喘生物学靶标
哮喘内表型的异质性,是遗传易感基因、环境诱发因素与宿主免疫反应,通过不同分子免疫生物学机制产生不同的气道炎症亚型,包括T辅助淋巴细胞(Th)2型、非Th2型和混合细胞型。Th2型分为过敏性和非过敏性炎症。Th2型过敏性炎症主要包括嗜酸性粒细胞(EOS)性炎症,非Th2型主要分为寡粒细胞型和中性粒细胞型。过敏性炎症始发因素是过敏原作用于炎症细胞(EOS、肥大细胞、树突状细胞)分泌白细胞介素(IL)‐4、IL‐5、IL‐13、前列腺素(PG)D2、IgE等细胞因子和抗体。非过敏性炎症始发因素是污染物和微生物,作用于炎症细胞(EOS、肥大细胞、固有淋巴样细胞2型)分泌IL‐5、IL‐33、PGD2、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(TSLP)等细胞因子。中性粒细胞型炎症的始发因素是污染物、氧化应激和微生物,作用于中性粒细胞等炎症细胞,分泌IL‐17和趋化因子配体(CXCL)‐8等细胞因子。混合细胞型兼具Th2型和非Th2型炎症特点。研究发现,儿童期哮喘与成人不同,急性发作时以EOS炎症为主(50%),包括混合型炎症占总数85.7%,而稳定期以寡粒细胞型炎症为主。并且EOS炎症在儿童过敏和非过敏哮喘中均可发生。重症哮喘可形成气道重塑,潜在的炎症机制更加复杂。研究显示在重症哮喘患儿活检中发现大量黏液栓和EOS炎症,并可见气道网状基底膜增厚(最小年龄2.6岁)和气道平滑肌增厚,提示气道重塑不可逆改变在年幼儿期已经形成。
重症哮喘患儿诱导痰中IL‐10、干扰素(IFN)‐γ、粒细胞巨噬细胞刺激因子(GM‐CSF)和肿瘤坏死因子(TNF)‐α水平和中性粒细胞可显著增高。全基因组关联研究(GWAS)明确了多种基因多态性与哮喘上皮功能、固有及适应性免疫相关。未成熟CD4+T细胞在不同炎症介质诱导下分化为不同亚型炎症细胞,包括Th1、Th2、Th17、Th9、Th22,并相互作用形成哮喘复杂的炎症网络。研究发现,与IgE水平相关的编码IL‐13、IL‐4/IL‐4RA、高亲和力IgEβ链(FCER1B)和β2肾上腺素能受体(ADRB2)四种基因间相互作用与哮喘发病相关;同时携带
这四种基因纯合子可增加哮喘风险(OR=13.55)。表观基因组学研究发现,出生后婴儿全血中14CpG寡脱氧核苷酸位点DNA甲基化降低与儿童哮喘发病相关,提示表观遗传机制可能是介导儿童哮喘相关母体遗传的危险因素。
之后还陆续发现6种CpG不同甲基化水平与胎儿期PM暴露有关,其中低水平甲基化的IL12B与减少急诊次数有关,高水平甲基化的皮质醇基因(CORT)与减少口服激素有关,提示不同的IL12B和CORT甲基化水平与持续期哮喘患儿吸入治疗反应相关,其药学‐甲基化水平可用于鉴定药物治疗敏感度的指标。关于婴幼儿毛细支气管炎与哮喘的关系,研究发现IL‐10基因多态性与5~7岁前哮喘发病有关。全基因组学分析发现,低收入家庭哮喘患儿CD14+单核细胞中检测到高表达的抗菌药基因和促炎相关转录因子,CD3+/CD4+Th细胞低表达可上调Th2和Th17活性编码IFN‐γ和TNF‐α基因的转录因子,提示社会经济状况通过炎症亚型的分子机制可影响哮喘的发病。
三、基于靶向治疗有望破解重症哮喘难题
儿童哮喘的治疗方案可分为标准疗法、靶向疗法和其他疗法。多数哮喘患儿经GINA推荐的标准疗法控制良好,使用高剂量吸入型糖皮质激素(ICS)治疗不能控制的哮喘患儿,可考虑加用长效β受体激动剂和白三烯受体调节剂,也可口服泼尼松龙治疗;但少数难治性哮喘患儿,经GINA推荐方案治疗后仍不能控制。基于哮喘炎症亚型的生物学靶向治疗,将成为破解难治性哮喘可行的方法。目前有5种生物制剂可用于儿童哮喘,研究结果显示,靶向治疗可减少哮喘急性发作和激素用量,改善症状和肺功能:(1)抗IgE奥马珠单抗(Omalizumab):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(FDA)和年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(CFDA)批准可用于6岁以上儿童中重症哮喘。根据患儿治疗前测定体重和血清总IgE,利用剂量表确定合适剂量、给药频率(2周1次,或4周1次)和疗程。正规治疗12周至16周后观察哮喘控制情况,若哮喘控制明显改善继续用药;若哮喘控制欠佳需停药。治疗后过敏反应约0.2%。(2)抗IL‐5美泊珠单抗(Mepolizumab):年FDA和年在欧洲批准可用于6岁以上儿童重症EOS型哮喘,近6周内查血EOS计数≥/μl,或近12个月内/μl。用法为每次mg,每4周1次皮下注射,极少数可发生过敏反应和带状疱疹。(3)抗IL‐5受体贝那利单抗(Benralizumab):年FDA批准可用于12岁以上儿童重症EOS型哮喘,近12个月内查血EOS计数≥/μl,且2次以上哮喘发作。用法为每次30mg,每4周1次共3次后,改每8周1次皮下注射,极少数可发生过敏反应。(4)抗IL‐4α和IL‐13单抗(dupilumab):可用于12岁以上儿童重症哮喘,已进入Ⅲ期临床试验。(5)抗IL‐5瑞利珠单抗(Reslizumab):可用于12岁以上儿童重症哮喘,已进入Ⅲ期临床试验。研究表明,其疗效优于贝那利单抗。其他生物制剂如抗IL‐4和IL‐13单抗(Lebrikizumab)、PGD2受体(CRTH2)拮抗剂目前仅推荐用于成人重症哮喘。非Th2型靶向治疗,如抗CXCR2治疗重症哮喘尚无显著疗效。其他治疗,如增加ICS用量、茶碱、大环内酯类药、环孢素、细胞毒素及支气管热成形术在儿童使用均缺乏足够证据,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疗仅可用于尘螨过敏的轻中度稳定期哮喘。
重症哮喘患儿需重视定期门诊随访,至少每3个月进行疗效评估,包括哮喘发作的次数、症状和肺功能改善情况,并观察治疗反应。多数患儿存在吸入技术和治疗依从性问题,因此需反复检查吸入技术、治疗依从性、并发症管理、社会/情感需求、医患沟通和医疗护理情况。此外,重症哮喘的疗效还取决于哮喘外表型和内表型的异质性,需进行综合性评估,调整治疗方案后需再评估治疗反应,还需衡量医疗安全、经济负担和生活质量等情况。
总之,儿童哮喘的异质性特点,包括临床外表型、内表型的生物学靶标和治疗反应的不同。儿童哮喘的诊断首先要强调排除其他疾病;对于治疗困难的哮喘患儿,首先要解决影响疗效的各种因素包括吸入技术等问题;对治疗抵抗或难治性哮喘,需积极寻找生物学靶标尝试靶向治疗,并观察治疗后反应。靶向治疗策略是根据儿童哮喘异质性特点,首先基于GINA标准治疗方案,尽量避免诱发哮喘的危险因素;对儿童重症难治性哮喘,可酌情选用生物制剂进行个体化靶向治疗,并观察和评估治疗反应。未来哮喘研究的方向需转向更深内在炎症亚型、生物学靶标和遗传药理学机制的探索,儿童重症哮喘的靶向治疗仍充满希望和挑战,其研究成果将为儿童重症哮喘的个体化治疗提供理论依据。
资料来源:
苏苗赏,李昌崇.儿童哮喘的异质性与靶向治疗研究进展.中华医学杂志,,(6):-77.
感谢